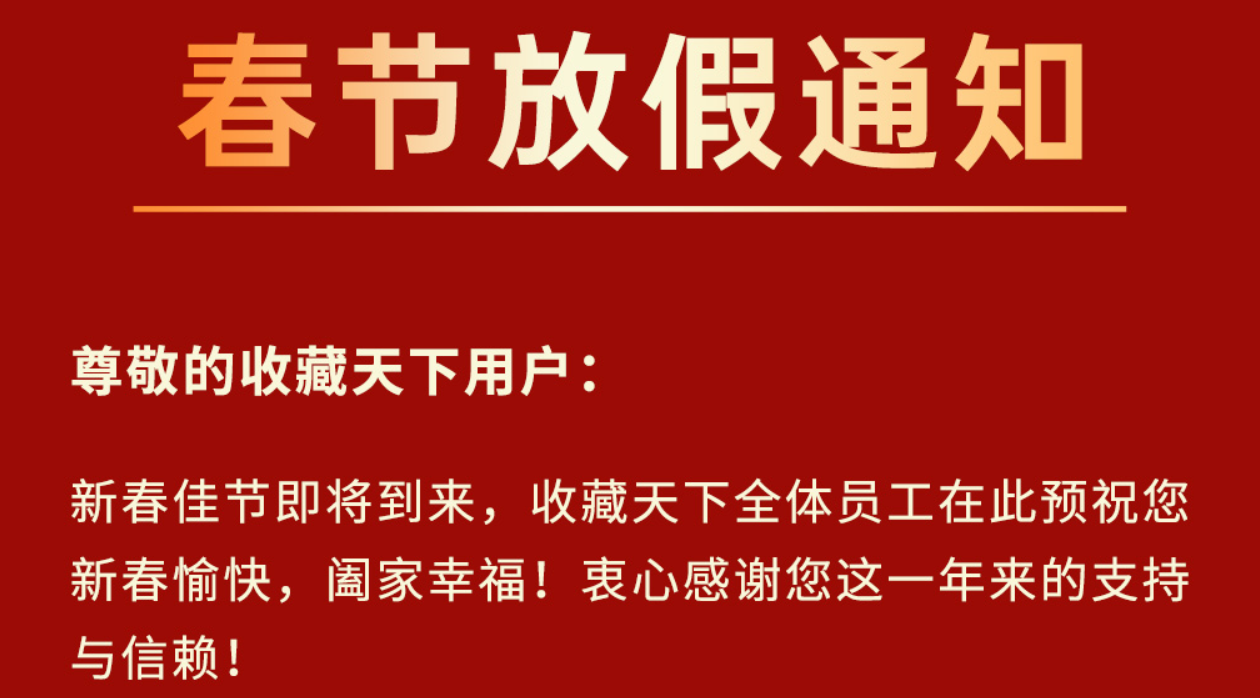徐(徐东树,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):我一直对您著名的“王小二”问题有兴趣,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就这个问题再向您请教一下、梳理一下。您说碑学的成份很复杂,既有技术含量高的,也有无技术含量的,碑学本身包含着多元标准。可否从社会学的角度寻找碑学兴起背后的推动力?宋代开始平民社会转向,贵族社会逐渐过渡到平民社会。到了明代,经济不断发展,市民阶层不断扩大。读中国艺术史的时候发现,求奇求异不仅仅在书法领域,也包括所有的艺术领域。华人德老师关于碑学的概括,很经典,就是无名氏书法,原来的帖学就是上层精英书法。什么是无名氏书法?其实它不是最底层的,我的理解是社会中层的艺术。到了明代还有一个底盘很大的下层文人,这些人的审美趣味比较庞杂,他们和市民有交集,出现了市民文人这么一个群体。还有市场的扩大,有奇特个性的东西,就好辨认好传播。
白(白谦慎,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): 我觉得,作为发展推动力,市场更可靠些。在写傅山的书里没有讲到这一点,但我认为求奇求异是求一种文化的“区隔”。你刚才讲到了上层精英,无名氏里其实有非常上层的人物,只是汉代不署名款。再早一点,钟鼎文,铸造的人是下层,但是书写的人肯定有贵族成份。所以,无名氏的概念非常宽广,它跟名家书法不一样,名家书法基本上是精英,无名氏就非常复杂了,没有名字的都可以归纳进去。这个概念需要详细地分化。比如石鼓文,它那种圆润厚重,其实是很精英的,不是没有技术含量的。这有别于碑学通常所强调的雄强稚拙,不同于那种“穷乡儿女”造像,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,当然也是最天真的那部分。
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,自称十鼓斋。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,仿军兵三阵命名为《先锋》、《中权》、《后劲》(如图,依左往右)秘藏之。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、最好的拓本,现皆流传到日本,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。2006年春三本同时来华参加上海博物馆的《中日书法珍品展》。
徐:您的“王小二”问题中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,您说“天真”很有趣但它不能自觉,要靠别人来发现。能发现“天真”的又肯定是受过训练的,但受过训练肯定少了天真,天趣就失去了。
白:是的。我谈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绘画里也存在。
徐:“无名氏”、“碑学”是很开放的概念,但“帖学”就很纯正,它不开放。碑学的颠覆性很大,它如果和平民、市场相关,那具体指的是什么?
白:就这颠覆性而言,通过“拙”也好,“奇”也好,“生”也好,和熟悉的经典产生一种距离感,达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,达到一种新意。但是这个游戏,又恰恰是最精英的人把玩,一般的老百姓写字不会追求“拙、生”,即使“拙、生”,他们也不会上升到美学的、理论的高度。这里面很大部分体现反“俗”的概念。实际上,旧的方法被经典化之后,又不断地寻找出新的东西,不断地重来,它跟传统经典的承袭性不太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断裂,碑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也就在这里。
徐:您这逻辑很清楚了。
白:这些我在书里没有写到。你讲到市民化、整个经典的扩大,士子群体、读书人的扩大,而碑学是这个背景下一种新的区隔化,是精英的一个新的竞争游戏。和谁竞争?和一般民众的区隔。薛龙春作过一个发言,我觉得有道理,他说,晚明到清初写异体字的风气,更多的是精英之间的区隔,就是要讲我和你不一样。
徐:您谈到区隔,我理解就是布尔迪厄的区隔,这里面包含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视野。我还关心另一个问题:中国学界有一批“新史学”学者,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是其中的一位代表,他们还有一本《新史学》的刊物。杨最近在《读书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很有意思,文章跟您这几年反复讲的史学观相近。他们15年前有一种强烈冲动,要向西方史学靠拢,要抛弃“旧”历史研究方法。15年沉淀之后,他们发现史学研究强调方法新旧不再重要,世界化和本土化的樊篱可以拆除,新史学留下的“厚描述”(研究中怎么尽可能把相关材料与问题挖掘得更丰满深刻)这个新旧其实是共通的。新的和旧的都可以做得很好。就像您的傅山研究,既包含很新的东西,也包含很旧的东西,两者没有冲突。
白:对,一颗好的原子弹和一把好的手枪都是好。或者,完全都是旧的方法,很纯的“旧”也行。
徐:您怎么理解做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呢?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经验吗?
白:其实就是要对研究材料足够熟悉。有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很得意地跟我说,傅山的《霜红龛集》他完整地看过三遍,我不太好意思对他说,我看过30遍都不止了。

徐:比如您谈过的汪世清先生,他的研究一点新观念都没有,就不好吗?肯定不是这样的,他对明清艺术史料的娴熟把握就可能解决很多历史问题。现在那群新史学的精英们,已经没有方法论的焦虑了,这当然是学科的成熟。反观书法史,我觉得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听到了一些争论,这些争论至少还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论思想和材料之间的关系,仍存有轻视思想的言论。其实偏废谁都不对。
白:书法史的情况相反,材料派和乾嘉学派是反过来占优势。确实偏废谁都不对,要有新的视野,完全可以用两者结合的方法来做。我最近准备发在浙江大学一本刊物上的文章(《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》),差不多六万字,整个都是考证和叙述,余论讲到他的收支决定了他的收藏策略,讲他的收藏策略和中国艺术研究的转型,但文章的前置部分全是考证。我写的东西也都是考证,谈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考证获得的。
徐:虽然您也是在考证,但是,考证后面有关怀,有理论思考,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。您3月10日在苏州博物馆作的演讲《信息、票号、运输——晚清收藏的网络要素》以吴大澂为例,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,揭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清后期收藏世界——私人收藏家如何获得异地古董的信息?成交后如何付款?又如何取得所购古董?如何将藏品带到任何之地?受什么条件制约或支持?您所关注的材料、研究的角度很特别,却都是用考证的方法,提出了很有新意的问题,还可以跟其它学科的学者对话,体现共同的关怀。
白:我的想法是,用考证的方式来做新的主题。如果没有其它的关怀,仅仅考证,主题就显得比较小。考证是可以发现理论价值的。前面说的争论是无谓的。当然有一种思考,和材料没特别大的关系,就是“纯”理论思考,那种情况归另外一套,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争的。你看,德国人有那么完善的抽象思维,但他们的考证也是很厉害,如考证版本学、训估学,他们似乎并不为理论和考证之类的问题发生争论。中国人自己争,争得无聊了。在中国,纯理论不够纯,没有达到“我就是纯的”状态,却老想要指导实践。一旦要指导实践的时候,那些实践的人就觉得你是隔靴搔痒。在西方,理论是另外一个学科,就不存在冲突了,整理文献的就归整理文献。在西方,你可以看到,学者中很少专门教美学的,也没有专门教艺术史理论的,但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会涉猎哲学和理论书籍,关心这一研究。真正的艺术史理论,又恰恰常是艺术史学家份内的事。像潘诺夫斯基,巴克森德尔,本身是艺术史学者,却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。历史学者去关心理论,理论学者把历史结合起来,这两者应无冲突。我研究中国书法史仍可以写理论的文章,但我基本上是以史学为主。
徐:理论或者历史,由于关注点不一样,各自有所侧重而已,实际上,他们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关怀。您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,您借助于社会学的视角来做历史研究,您也关心思想,涉及美学。
白:像“娟娟发屋”问题,反而在当代艺术中关心的比较多,像策展人鲍栋他们这些人。书法界里有些人觉得自己比较前卫,其实没有触及当代文化的问题。这就麻烦了,其实他们的东西并不前卫,如果他们真正读懂《娟娟发屋》的话,就会理解我思考的比他们前卫得多了。遗憾的是,他们没有读懂。
徐:因为他们可能不是在一个大的当代文化场的共同视域中思考。您谈到的,就是当代文化标准多元化之后,怎么认定艺术,怎么认定艺术跟生活跟权力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恰恰是当代艺术最关心的课题。
白:对,这是他们最关心的课题。当代艺术想打破它和生活的关系,打了半天也打破不了。
徐:这是个悖论,也是您一直谈论的问题,人没有办法揪住头发把自己拎起来。从傅山开始您就一直在提这个问题。
白:这是书法界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像毕加索也好,康定斯基也好,他们在摹仿小孩子,康的摹仿是藏起来的,毕没藏,他就是直接和女儿合作。康定斯基是把当代小朋友的画藏起来,但西方并没有收藏小朋友画的传统,人类早期留下的岩画是早期原始人的不是小朋友的,所以他们找不到古代的例子。中国人很有意思,恰恰留下很多古代书写的遗迹,穷乡儿女造像,那种无古无今的,没有进入技术含量体系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,与古为徒的这种文化倾向,就引进来了,把“古”自然地当作典范,并将其扩大化,到最后变成“古”的就好的,不要再追问其它了。“娟娟发屋”为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角度。
徐:您曾经说到过两个有意思的问题。一个是史料当中“区别对待”的问题:古代与当代由于现实利益关系不同,有不同的价值认定。另一个与中国当代艺术遇到的难题相近——就是艺术标准和边界的问题。
白:是的。文学批评家李陀,他看了我的文章,对我说,当年去收集民歌,想着能不能原汁原味地保留。但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:如果不去升华它,它最原始的东西就呈现出直白的,赤祼祼的,没有任何掩饰的甚至是两性之间的东西;改造还是不改造?但是,民歌和我们的“穷乡儿女造像”是不一样的,民歌是一个自觉的创作,民歌再粗犷,也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创作,也就是说,民歌的作者和民歌的唱者意识到自己美;写“穷乡儿女造像”的却不会发现自己美,很可能觉得自己丑。发现它有意思,那是精英们。民歌,是精英们觉得美,民间唱者也觉得美。书法的例子具有特殊性。
徐:这和刚才谈到毕加索与小朋友的问题很像。专业技术训练和天趣之间的关系,是精英和素人之间的关系,有专业技术就没有天趣,有天趣就没有专业技术。天趣是不自觉的。这个您多次谈过。我还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:一旦碑学带来了多元标准,有技巧和没技巧都可以被推崇的时候,实际上确实会导致——因为它自身有矛盾——标准不是分化而是模糊了。
白:这个标准的模糊,在当代首先在于精英本身丧失了他们的能力,因为他们对毛笔书写的生疏。清代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康有为他们要区分天趣和江湖容易得很。现在的人,失去能力了。
白谦慎 《辛稼轩西江月》 28.5×16cm 纸本 2017年
徐:随之而来的问题是,标准一旦真正的多元之后,会不会带来精英标准的塌陷?
白:精英标准的失落,不是多元的结果,而是精英阶层撤出了书法界的结果。我表述过这种想法,就在《从吴大澂到毛泽东》的文章里。
徐:精英确实已经离开了书法这个领地。不仅书法,整个当代原来上层的雅文化都变成了弱势群体。因为要掌握传统雅文化的素养和技艺有相当的难度。
白:当精英离开书法,有人只要忽悠了媒体,忽悠了领导,好象就可以呼风唤雨了。忽悠大众是容易的。大众也不懂,媒体也不懂,领导也不懂,三不懂造成了一些乱象。在清代,大家捧着乾隆皇帝,但是谁都知道乾隆皇帝写得不好,底下大臣们都知道,想唬他们没门。
徐:那个时候文化精英掌握话语权。可是大众文化时代,情形有些变了。德国学者顾彬在中国讲演时说过,在德国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,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构成很大的冲击。
白:但是中国有不一样的地方,比如,中国书法家协会,它的技术门槛一直在那个地方,江湖的人进不去。实际上的分野,是学者这个群体。现在所谓的学者书法,我是不提倡的。因为大多数学者其实字很差,有些甚至是乱写的,那个才叫江湖书法。学者只是一个身份,跟书法没有什么关系。过去,学者都动毛笔,能够从中挑一些比较好的(也不是都好),比如马一浮,把他当作学者书法的代表。过去的学者书法中,一般水准的多,但恶俗的基本没有。你看中国书法家协会中推出来的,技术完美的挺多,特别深入的少,但是绝对不能叫江湖,江湖的人进不去,第一关就先给刷掉了。那种江湖的,个别的在媒体上翻一下浪就不见了。
徐:现在整个文化的分层确实有些紊乱,中低层的那些文化和艺术在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,精英的艺术反而比较弱势。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。
白: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特别是真正好的学者书法,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懂。那种特别的,比如说,夏承焘的字看起来拙拙的很蕴藉,不是很漂亮,也没有什么人会去模仿,现在很难继承,很难被人欣赏。

徐:我看章汝奭先生的字,他的小楷小行书,很文气很有味道,他也不以书家面目临世,却是真下了工夫。
白:他花的功夫比专业书法家还多。
徐:读书人又在艺术上很有造诣,他这种书法在这个时代是绝对的弱势群体。但是在康有为那个时代肯定不是,精英们都明白,这样子好。
白:如果这种书法依然被信奉的话,就等于没变嘛。现在精英撤退了,精英在整个书法群落中,学者在书法中占比本来就很小了。我曾经把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删掉了,因为,可能有些人听了刺耳。我说,最聪明的人离开了书法。
过去,最聪明的人都学书法,聪明人的基数大,从里面会冒出一些尖子。现在学书法的人不能说不聪明,但从整体来讲,跟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的能力相比,那点聪明是不够的。现在艺术院校专业的文化分数偏低。脑子最聪明的那些人做什么去了?研究“两弹一星”去了,干金融去了,弄国际法去了,……北大一两万学生,书法社只有几十人,基数太小了。学习一忙,练习的量不够。不能说,读书好,字就自然写得好,这也是没道理的。这样反而降低了书法的门槛。
过去的人,为什么不讲文化修养,王羲之需要讲文化修养吗?士族大家,从小就有文化底蕴,贵族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训练。讲究文化修养,恰恰是在宋代,那是世俗化形成的时候。现在,该变也就变了,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研究。
徐:在当代,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文化分层的努力,把真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区分开?
白:分不了的。现在学术界的评价系统紊乱。哪怕理工科的评价体系都有一些问题。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展览要评比就需要评委库。1986年出国前,我当过全国第二届中青展评委。丛文俊、黄惇、华人德、曹宝麟等评委,都是正儿八经的学者。现在,现任的评委基本上是从得了几次奖的得奖库中挑出来当评委,大多不是学者,都是写字的。想转变这套评价体系,是很困难的。
中国书法家协会培养了一个新的书法精英阶层,它跟传统的文化精英阶层是两回事。必须要看到现在体制的力量,它起了很大的作用,西方没有中国书协这个系统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,就是现在的艺术教育系统。我在为王家葵的书作序时说过,文人士大夫退出之后,精英空白被谁取代了?就是艺术教育体系去培养学生填补。现在在高校教书基本上是要有学历的,以前,书法家当高校的书法老师如沙孟海、陆维钊是没有这个艺术学历的,但以后讲究这个学历。这会阻碍社会上很有才华的人进入书法高等教育的可能。就目前来说,字写得特别好,在大学里教书,还可以转过去做书法。还有孙晓云、鲍贤伦等,也不是从新系统出来的。现在新旧体系并存,也有交融。但是再下一代,就不一样了。就像我们也写字,现在要想去得奖,根本不会被评委认可。现在特别讲技法,一笔一画临得像不像,到不到位。
说到学者书法,真正学者型的字,是很有个性的,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,姜亮夫的字就很有个性;朱光潜、茅盾、郭沫若的字,全是一人一个样。我与华人德、曹宝麟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,字写得都不一样。但现在艺术院校培养出来写的字常常没有个性。他们看起来多元,其实没有个性,是多元化COPY(复制)多元化,反而成了一种“多元化模式”。就像他的衣服比你多,今天穿一件,明天穿一件,看起来有个性,还不如整天只穿一件自己设计的蓝大褂,才是真正的个性。
徐:经济发展到今天,我们会不会孕育出一个新的文化精英阶层?
白:看吧,看中国今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趋势。现在生产力这么发达,中国会涌现出大量的富二代、中产阶级,会出现新的文化阶层。新的情况会怎么样,中国今后的格局,真的不知道、说不准。
本文由收藏天下转载于网络,仅供阅读,版权归原作者
 登录
登录